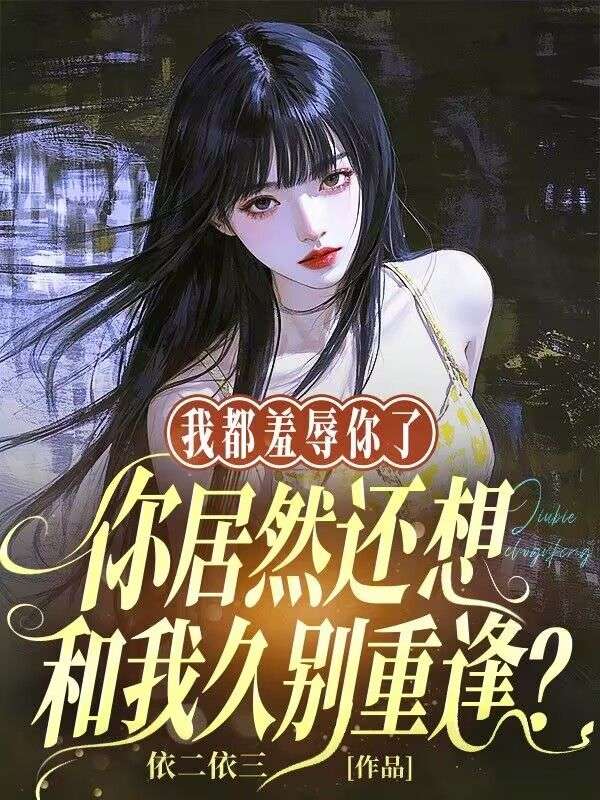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
第8章
宋佳琪把行李箱拖進屋,又手腳麻利地鋪好床,這才湊到許素心身邊,壓低了聲音問。
“姐,那個開邁巴赫的,真就這麼算了?連賠償都不要了?”
許素心正在疊衣服的手停頓了一下。
宋佳琪一臉不信,自顧自地嘟囔:“他看著可不像什麼好人,渾身上下都寫著不好惹三個字。這種人會這麼好心?我不信。”
“他......”許素心張了張口,最後隻吐出幾個字,“他以前不是這樣的。”
“以前?”
“嗯。”
以前的沈柏川,是真的很好。
好到她現在想起來,心口都還會泛起一陣陣密密麻麻的酸澀。
那時候他還是個窮學生,冬天兩個人擠在出租屋裏,他會把身上唯一一件厚外套脫下來給她,自己凍得嘴唇發青,還笑著說自己年輕火力旺。
她隨口說一句想吃城南那家的蛋糕,他就會坐兩個小時的公交車去買回來,小心翼翼地護在懷裏,生怕擠壞了一點。
他會把省下來的錢,給她買一支廉價卻亮晶晶的發卡,然後笨拙地別在她的頭發上,告訴她,她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姑娘。
那時候的沈柏川,眼睛裏全是她。
可現在,他連多看她一眼都覺得厭惡。
宋佳琪見她出神,臉上的表情難看,以為她又在想程和潤那個渣男,趕緊岔開話題:“行了行了,不想了!離了就好!今晚姐你好好睡一覺,明天又是新的一天!”
許素心扯出一個勉強的笑,點了點頭。
這一晚,她睡得並不安穩。
陌生的床,窗外偶爾傳來的車聲,都讓她輾轉反側。
腦子裏一會是沈柏川冷漠的臉,一會是程和潤猙獰的表情,最後,畫麵都定格在女兒絮絮蒼白的小臉上。
她猛地坐起來,摸了摸額頭,全是冷汗。
天還沒亮,她就再也睡不著了,索性輕手輕腳地起床,洗漱過後,跟宋佳琪留了張字條,便去了醫院。
清晨的陽光透過病房的窗戶灑進來,給冰冷的房間鍍上了一層暖色。
“媽媽!”
程絮看見她,眼睛立刻亮了起來,掙紮著想坐起來。
“慢點。”許素心趕緊放下手裏的保溫桶,過去扶住女兒,又在她背後塞了個枕頭。
“媽媽,你來啦!”絮絮開心地拉住她的手,小臉因為興奮泛著紅暈,“李醫生昨天跟我說,我們已經把錢都交齊了!以後都不用擔心醫藥費了!是爸爸給的嗎?”
孩子天真的問話,讓許素心心臟的位置猛地抽了一下。
她看著女兒充滿期待的臉,那個不字堵在喉嚨裏,怎麼也說不出口。
她不能讓絮絮知道,她的爸爸已經徹底拋棄了她們。她不能讓這麼小的孩子,在承受病痛的同時,還要承受家庭破碎的打擊。
沉默了片刻,許素心低下頭,打開保溫桶,嗓音有些發啞。
“嗯,是爸爸。”
“我就知道!”絮絮立刻歡呼起來,蒼白的小臉上滿是喜悅,“我就知道爸爸還是愛我們的!他是不是跟你和好了呀,媽媽?”
“等我病好了,我們一家三口,又可以一起去遊樂園了,對不對?”
勺子在碗裏攪動著,發出輕微的碰撞聲。
許素心喉嚨發緊,勺子裏的粥都燙了,她卻渾然不覺,隻是一個勁地吹著。
等再抬起頭,她才勉強擠出一個笑。
“對,絮絮快吃飯,吃了飯才有力氣早點好起來。”
她舀起一勺粥,送到女兒嘴邊。
絮絮乖乖地張開嘴,眼睛笑得彎彎的。
許素心一口一口地喂著,動作有些機械。
看著女兒吃完藥後沉沉睡去,許素心才鬆了口氣。
她替絮絮掖好被角,在床邊坐了很久,直到自己的肚子不合時宜地叫了一聲,才輕手輕腳地拿起保溫桶。
醫院的走廊永遠是那股消毒水的味道。
她路過樓下小花園,看見幾個差不多大的孩子在滑梯上笑鬧,腳步頓了一下,很快又繼續往前走。
等她提著剛打好的飯菜回來,推開病房的門,裏麵安安靜靜。
床上沒人。
被子疊得整整齊齊,絮絮看到一半的童話書被扣在枕頭邊。
她心頭一跳。
“絮絮?去洗手間了?”
她推開衛生間的門,裏麵空空蕩蕩。
一種不祥的預感攥住了她的心臟。
她衝出病房,抓住一個路過的小護士就問:“你好,請問12床的小孩兒呢?”
小護士愣了一下,搖搖頭:“不清楚,我不是這層的。”
許素心鬆開手,茫然地站在走廊中間,正要去找相熟的護士,另一個護士急匆匆地從拐角跑過來,一眼就看見了她。
“程絮媽媽!你可算回來了!”
“你女兒剛才在樓下暈倒了,剛送去搶救室!”
手裏的保溫桶掉在地上,飯菜灑了一地,她卻毫無知覺。
她拔腿就往樓下衝,身體因為恐懼而抖得厲害。
為什麼會暈倒?
早上還好好的......
她瘋了一般地衝到一樓,也顧不上等電梯,直接從樓梯跑下去,終於在走廊的盡頭,看到了那亮著紅燈的搶救中。
門緊緊地關著,隔絕了內外兩個世界。
許素心腿一軟,扶著冰冷的牆壁,才沒有摔倒。
她的絮絮......她的絮絮在裏麵。
搶救室的紅燈,已經亮了三個小時。
許素心靠著走廊冰涼的牆壁,全身的力氣都被抽空,整個人順著牆麵滑坐在地。
終於,那扇緊閉的門開了。
一個穿著白大褂的醫生走了出來,摘下口罩,臉上滿是疲憊。
許素心猛地撐地站起,踉蹌著撲過去:“醫生,我女兒怎麼樣了?絮絮她怎麼樣了?”
醫生看著她,搖了搖頭,表情沉重:“我們盡力了,但孩子的情況很複雜。她本身底子就弱,這次突然昏厥,應該是遭受了什麼重大的精神打擊,引發了急性並發症。現在的情況非常危險。”
許素心的世界轟然倒塌,眼前陣陣發黑。
“怎麼辦?醫生,求求你,救救她,救救我的女兒!”
她抓住醫生的胳膊,指甲摳進了對方的衣袖裏。
醫生歎了口氣,扶住她搖搖欲墜的身體:“常規的治療手段已經到了極限。現在唯一的希望,是能請到國內兒童血液病的頂尖專家,薛教授。隻有他或許還有辦法,但薛教授的行程排到了明年,而且從不輕易出診......”